2015-08-15王剑王剑的角度王剑的角度王剑的角度[img][/img] 微信号 wangjianzj0579
功能介绍 投研就像摄影,永远胜在角度。分析师、摄影师王剑,欢迎交流。

随笔 2015-8-15
东方证券 银行业首席分析师
王 剑
核心观点
(1)银行机制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;(2)银行改革被倒逼而成;(3)银行改革又需要政策银行改革、国企改革、直接金融发展等相配套。 学术界早已把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历程归纳成优美的理论模型,我们尽可能将其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。当然,模型只是对现实的模拟。一、国有银行:资本金迷局 大家先回忆一下,1990年代末期,当时四大银行的不良率是30%多。而银行的股东资本占总资产比例仅为10%左右,其余全是负债(主要是存款)。换言之,这些银行早就资不抵债了……可如果你去大街上跟别人说:“某行资不抵债了,赶紧把钱取出来。”你一定会被当成神经病。
换言之,我国的银行是不需要资本金的。
这就是学术界常称的国有银行“资本金迷局”。原因也很简单,因为我们的银行是有国家担保的。即使国家不说,我们也是这样相信的,这叫隐性担保。
我们将这一迷局构建成一个模型:国有银行不需要资本金,存款人相信国家会担保他们的存款,所以存款就是资本金!所以我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:
 政府其实是以国家信誉入股了银行,入股就要有回报。政府获取的回报,是通过其对银行、国企的控制,根据政府意志安排银行信贷投向,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(注意,有时候不一定是银行利益最大化)。这些回报包括推行经济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、救助国企、维持社会稳定(比如安定团结贷款,给困境国企发贷款用于发工资),不一而足(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不正当用途)。这些回报不是直接货币性的,是对国家的益处,我们称之为“控制权回报”。 政府其实是以国家信誉入股了银行,入股就要有回报。政府获取的回报,是通过其对银行、国企的控制,根据政府意志安排银行信贷投向,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(注意,有时候不一定是银行利益最大化)。这些回报包括推行经济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、救助国企、维持社会稳定(比如安定团结贷款,给困境国企发贷款用于发工资),不一而足(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不正当用途)。这些回报不是直接货币性的,是对国家的益处,我们称之为“控制权回报”。
所以,国有银行其实是一个投融资通道:老百姓的钱存进来(国家信誉担保其安全),再按国家的意志投出去(获取控制权回报)。
很显然,只要国家信誉不崩溃,那么资本充足率、不良率、流动性管理这些概念都是废话。
 但是,毫不意外,这样投放的贷款质量很差,不良率超高,高到一定程度银行就干不了活了。为此,政府用两种手段弥补: 一是,设定固定的存贷款定利率,保障银行稳定利差(称“特许利差”或“特许利润”),用以弥补不良损失。 二是,如果特许利润还不够,那么政府直接出资救助,包括剥离不良及注资。这是国家在履行其对存款的担保,也就是国家为维护其信誉付出的成本,也就是担保成本。 所以,这一模型便是:(1)银行以国家信誉入股银行,担保存款; 但是,毫不意外,这样投放的贷款质量很差,不良率超高,高到一定程度银行就干不了活了。为此,政府用两种手段弥补: 一是,设定固定的存贷款定利率,保障银行稳定利差(称“特许利差”或“特许利润”),用以弥补不良损失。 二是,如果特许利润还不够,那么政府直接出资救助,包括剥离不良及注资。这是国家在履行其对存款的担保,也就是国家为维护其信誉付出的成本,也就是担保成本。 所以,这一模型便是:(1)银行以国家信誉入股银行,担保存款;
(2)国家干预银行信贷投放,并以此获取控制权回报;
(3)会有不良产生,政府设定特许利差用以弥补;
(4)如果特许利差不够弥补,则政府出资救助银行(剥离不良,注资),这是国家履行对存款的担保,是担保成本。
通俗讲,就是政府开了银行,担保其存款(保证资金来源),并要求银行为政府意图干活。为此产生的不良,首先由政府设定特许利差给予弥补,不够还有政府最终负责。 在政府担保背景下,银行几乎不用担心存款来源,也不用担心存款的偿还,它们只需要拼命放贷赚钱,亏了国家兜底。 这是一个迷局。啥叫局?局的特点,就是没有强外力干预的情况下,或者内部各方平衡还能维持的情况下,这局会自行持续下去,没完没了。我们最终看到,在这一迷局下,政府一轮一轮地救助银行,这个局演变成了“注资怪圈”。1998、2003年两轮剥离与注资,耗资巨大。二、效果不彰的渐进式改革 我们假设政府也是个理性的参与者,也要考虑成本与收益。对面上述这一个局,国家的收益是控制权回报,而付出的成本是担保成本(为维持信誉而要支付的)。成本收益公式 = 控制权回报 / 担保成本(也就是信誉成本) 而随着银行总存款、总资产越来越大,政府的担保成本也越来越高。所以,政府考虑破这个局,目标是退出政府担保,按现代企业制度办银行。国家继续当股东,把真金白银拿出来当银行的资本金,也不再干预银行经营(让银行成为独立自主经营的主体),然后国家只作为股东,收取股东回报。成本收益公式 = 股权收益 / 资本成本 这就是邓公所谓的“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”。
按此思路,循序渐进的改革很早就开始推行,但进展不大。2004年左右,各大银行开始股改,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,后来陆续上市,进展相当完美,我们以为原来的局已破,我们的银行将直站康庄大道。
显然,这想法太天真了。2009年“四万亿”刺激横空出世,我们悲伤地发现,银行还是按政府指示放贷款。生活教育了我们:股改并没什么X用。
我们来分析其改革内容,来了解为何没什么用:(1)股改并上市:其实就是混合所有制,国家用真金白银出资,还引进其他投资者,降低官股比例。但只要国家还是绝对控股,老百姓还是相信国家担保,国家信誉无法退出。所以,国家信誉的存在使“混合所有制”的效果难以彰显,除非像台湾1980年代末一样,公营银行彻底私营化。
(2)完善公司治理:股改后,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(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管理层)已经搭建,但并没有真正的职业经理人,金融干部均由国家委派,银行不可能脱离政府干预。
(3)借款人方面:只改了银行这一端,而借款人——占比最大的是国企——没有市场化改革,那么只能一切照旧。
“四万亿”后形成了大量的地方债,政府没有直接出手剥离救助(因为这就相当于承认我们还是处于原来的“注资怪圈”里,承认了贷款是政策性的,那么银行就彻底不用管风控之事了,会有道德风险)。拖延几年后,2014年10月终于出台了“由省政府发债募资,用于置换原来的地方债”的方案(国发〔2014〕43号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)。
由于省政府信用基本上等同于中央政府信用,所以这其实还是政府剥离,我们依然活在“注资怪圈”里。很显然,破局并不彻底。国家用真金白银注资了,但国家信誉不可能彻底退出,国家是既出资本又出信誉;银行信贷投放自主性大幅提高,商业性贷款多了,但干预仍在,政策性信贷仍有。综上,不管是分子还是分母,改革都只改个半吊子,同志仍需努力。
 事实上,这种半吊子状态比原来更恐怖:贷款中商业性比例越来越高,这些贷款是能赚钱的。然而,资金来源仍由国家仍保证,用这些资金放贷赚的钱却是自己的。这相当于国家为银行支付一笔无形的补贴,弥补了部分信用风险。这种情况下,银行的通行做法必然是:拼命拉存款,然后放贷赚钱! 事实上,这种半吊子状态比原来更恐怖:贷款中商业性比例越来越高,这些贷款是能赚钱的。然而,资金来源仍由国家仍保证,用这些资金放贷赚的钱却是自己的。这相当于国家为银行支付一笔无形的补贴,弥补了部分信用风险。这种情况下,银行的通行做法必然是:拼命拉存款,然后放贷赚钱!
站在国家的角度,则是:继续为存款提供担保(这是有成本的),而控制权回报的比例下降(因为政策性贷款比例是下降的)。所以,这笔买卖对国家来说越来越不划算了。
所以,这个局内部越来越不平衡,终会破的。
三、破局:高货币化率迷局 这个局终究是会有个头的。存款总额已达130万亿元,金额惊人,照此下去,政府救助成本会越来越高,终有一天要崩溃的。 救助成本有多高,从更宏观角度,我们可以看货币化率(M2/GDP)指标。 在我国,信贷投放是派生M2的重要渠道,M2除一部分由外汇占款直接投放外,大多是银行投放信贷、购债、非标等渠道派生而来的,我们将这些渠道都统称为广义信贷。所以,M2越高,代表着广义信贷存量越高,利息支出也越高。 而还利息的钱,只能来自这个国家每年创造的财富,也就是GDP。 所以M2/GDP可粗略地代表一个国家的杠杆。分子是负债,乘以利率就是利息总额。分母是创造的财富,还利息的钱得这里面出。M2/GDP越来越高,则付息压力越来越大。 随着市场化推进,GDP中国有部门占比下降,但M2却越来越高。万一出事,国家得救整个M2……所谓国家来救,具体操办人是央行,即最后贷款人。央妈也急了,力推存款保险,至少先转嫁一部分救助成本。
2014年,我国M2/GDP是200%。别的国家远没这么高,尤其是发达国家,M2/GDP到100%左右就回落了,不再上升,最后形成了一个均衡值,波动不大。
 罗纳德·麦金农在其经典著作中解释了这个均衡值。我们将其模型简化描述。银行的生意,是收贷款利率,先扣存款利率,再扣各项成本率,最后是其利润。贷款利率 – 存款利率 – 各项成本率 = 利润率 如果我们把合理利润看成股东的资本成本,包含到成本里,那么上式中的右项就成了“超额利润”。贷款利率 – 存款利率 – 各项成本率(包含股权成本) = 超额利润率 按照微观经济学原理,完全竞争市场中,超额利润为零。所以:贷款利率 – 存款利率 – 各项成本率(包含股权成本) = 0 再变换一下,右移:贷款利率 – 各项成本率(包含股权成本)= 存款利率 也就是说,等号左右两项相等时,达到均衡,M2/GDP的升势也就到头。 然后开始画图。S是存款曲线,假设存款利率越高,老百姓就存更多钱(所以曲线朝右上方)。D是“贷款利率-成本率”的线,利率越低(假设成本率固定),大家会贷更多钱(所以曲线朝右下方)。两线相交处就是满足“贷款利率–各项成本率(包含股权成本)=存款利率”条件的地方,对应的货币量A点就是最优的货币化率。 罗纳德·麦金农在其经典著作中解释了这个均衡值。我们将其模型简化描述。银行的生意,是收贷款利率,先扣存款利率,再扣各项成本率,最后是其利润。贷款利率 – 存款利率 – 各项成本率 = 利润率 如果我们把合理利润看成股东的资本成本,包含到成本里,那么上式中的右项就成了“超额利润”。贷款利率 – 存款利率 – 各项成本率(包含股权成本) = 超额利润率 按照微观经济学原理,完全竞争市场中,超额利润为零。所以:贷款利率 – 存款利率 – 各项成本率(包含股权成本) = 0 再变换一下,右移:贷款利率 – 各项成本率(包含股权成本)= 存款利率 也就是说,等号左右两项相等时,达到均衡,M2/GDP的升势也就到头。 然后开始画图。S是存款曲线,假设存款利率越高,老百姓就存更多钱(所以曲线朝右上方)。D是“贷款利率-成本率”的线,利率越低(假设成本率固定),大家会贷更多钱(所以曲线朝右下方)。两线相交处就是满足“贷款利率–各项成本率(包含股权成本)=存款利率”条件的地方,对应的货币量A点就是最优的货币化率。
 但在我国,上述很多假设并不成立。最重要的一点是,政府给予了银行补贴,弥补了银行的很多成本(比如存款担保就弥补了银行一项重要的信用成本)。我们粗略假设政府补贴了所有成本,那么D线就上移到D’线,相应地,最优货币量也从A右移到B。我国最优货币化率就提高了。 但在我国,上述很多假设并不成立。最重要的一点是,政府给予了银行补贴,弥补了银行的很多成本(比如存款担保就弥补了银行一项重要的信用成本)。我们粗略假设政府补贴了所有成本,那么D线就上移到D’线,相应地,最优货币量也从A右移到B。我国最优货币化率就提高了。
除了政府补贴外,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导致货币化率高企,比如:
1高储蓄率 社保不完善,养老教育医疗要花钱,我们每月领的工钱不敢乱花,要存起来,因而国家消费、投资不给力。高储蓄率意味着S线向右平移到S’,最优货币量从B点右移到C。
 2政府干预放贷 政策性贷款还是存在。而在上述银行注资怪圈中,银行也有放贷冲动(赚了是自己的,亏了是国家的),导致D’曲线进一步右移,最优货币量从C点继续右移…… 正因为上述这些因素,我国的货币化率远高于其他国家。而畸高的货币化率带来种种恶果。恶果1 货币政策传导困难。银行成了政策传导途径,央妈的宽松作用于银行间市场,却因为银行目前不敢放贷,流动性淤积于银行间,传不到实体。 2政府干预放贷 政策性贷款还是存在。而在上述银行注资怪圈中,银行也有放贷冲动(赚了是自己的,亏了是国家的),导致D’曲线进一步右移,最优货币量从C点继续右移…… 正因为上述这些因素,我国的货币化率远高于其他国家。而畸高的货币化率带来种种恶果。恶果1 货币政策传导困难。银行成了政策传导途径,央妈的宽松作用于银行间市场,却因为银行目前不敢放贷,流动性淤积于银行间,传不到实体。
 恶果2 恶果2
金融效率损失。政策性贷款或许对国家是有益的,但对银行未必,是对金融效率的牺牲。恶果3
风险集聚于银行体系,救助成本很高。国家也担心终有一天是救不了的。 毫无疑问,照此以往,终有一天是救不了的。所以,改革会被倒逼着实施。四、银行改革图景 在M2/GDP到达一个畸高的水平后,国家为存款担保的成本会很高,高过其收益,国家当然也意识这样下去谁都得玩完。所以,改革被逼得进行了。
改革不能单兵作战,得有全局观。就银行改革而言,至少得配合做四件事情:
1做大做强政策性金融 政府干预银行,指使其从事一些政策性业务,要想消除这种情况,必然需要政策性银行的发展壮大。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《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》,次年,三家政策性银行(国家开发银行、中国进出口银行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)均成立,从商业银行那里接走了政策性任务。
 但现实表明,这三家银行实力不足,无法把政策性任务全接走。2014年末,开行、口行、农发行总资产分别为10.3万亿元、2.4万亿元、3.1万亿元,三者合计不到16万亿元,占全部银行业总资产(172.3万亿元)为9%,占比很低。但就在上个月,有消息称,央行已向开行注资480亿美元,向口行450亿美元(此前则分别注资过320亿美元、300亿美元),财政部则向农发行注资1000亿元人民币。我们预计,随着这类机构发展壮大,承担政策性任务的能力越来越强,商业银行可逐步从政策性任务中脱身,从政府干预中脱身。2改革国有企业 国企目前仍然是银行的最大客户群体。一个巴掌拍不响,如果它们未改革,经营机制落后,经营效益恶化,那么银行改革肯定也改不到哪去。所以,目前举国上下关注国企改革,虽然路途艰辛,但它确实是银行改革过程中绕不过的坎。客户好了,银行才能好。3发展直接金融 鼓励企业直接融资,也鼓励居民投资这些新型金融工具。这简直是老生常谈了,投融资渠道多元化,别啥事都放银行,风险集聚。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就被淘汰了,银行也可继续为直接金融服务,比如资产证券化、资产管理等。 还有一点就是银行自身公司治理的改革。但这一点并不是难点。只要上述三点完成了,银行自身的改革是水到渠成之事。 我们用一幅图概括这一全景: 但现实表明,这三家银行实力不足,无法把政策性任务全接走。2014年末,开行、口行、农发行总资产分别为10.3万亿元、2.4万亿元、3.1万亿元,三者合计不到16万亿元,占全部银行业总资产(172.3万亿元)为9%,占比很低。但就在上个月,有消息称,央行已向开行注资480亿美元,向口行450亿美元(此前则分别注资过320亿美元、300亿美元),财政部则向农发行注资1000亿元人民币。我们预计,随着这类机构发展壮大,承担政策性任务的能力越来越强,商业银行可逐步从政策性任务中脱身,从政府干预中脱身。2改革国有企业 国企目前仍然是银行的最大客户群体。一个巴掌拍不响,如果它们未改革,经营机制落后,经营效益恶化,那么银行改革肯定也改不到哪去。所以,目前举国上下关注国企改革,虽然路途艰辛,但它确实是银行改革过程中绕不过的坎。客户好了,银行才能好。3发展直接金融 鼓励企业直接融资,也鼓励居民投资这些新型金融工具。这简直是老生常谈了,投融资渠道多元化,别啥事都放银行,风险集聚。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就被淘汰了,银行也可继续为直接金融服务,比如资产证券化、资产管理等。 还有一点就是银行自身公司治理的改革。但这一点并不是难点。只要上述三点完成了,银行自身的改革是水到渠成之事。 我们用一幅图概括这一全景:
 值得欣慰的是,政策性银行、国企改革、发展直接金融,这些措施目前均已在推进,这些都是银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,我们依然对中国银行业的未来保有信心。 值得欣慰的是,政策性银行、国企改革、发展直接金融,这些措施目前均已在推进,这些都是银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,我们依然对中国银行业的未来保有信心。
后记 最后,向大家隆重介绍本文的重点参考文献,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教授的《经济变迁中的金融中介与国有银行》。改革问题不是什么新课题,学术界早已有很成熟的成果,非常值得分析师们参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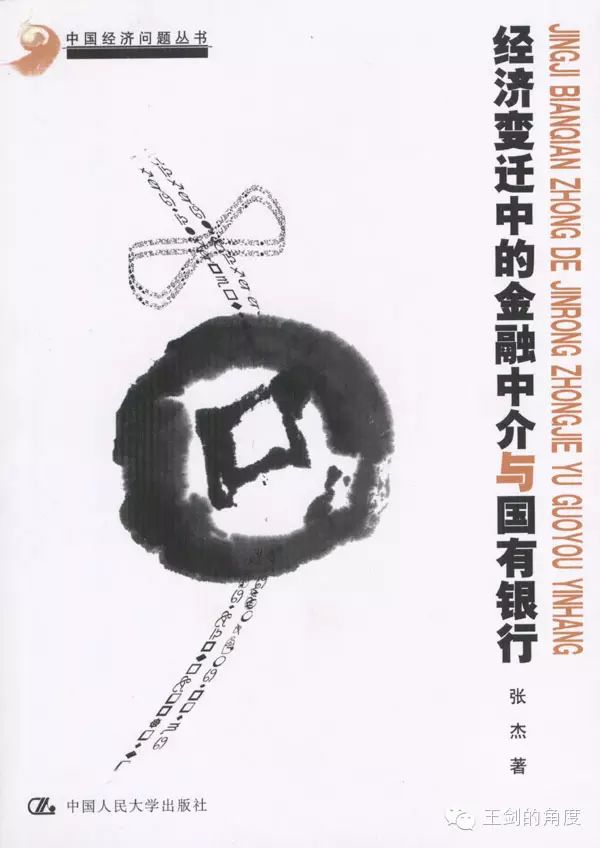 
阅读
举报
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
关注该公众号
|